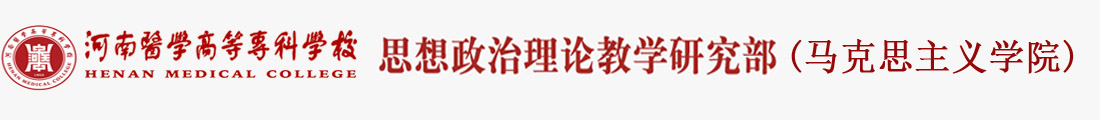[摘要] 公民教育当以培养时代公民为目标。公民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时代不同,公民的身份和素质要求不同。公民不是臣民,就在于他是一个权利主体;公民不是私民,就在于他参与公共生活。不同时代公民公共生活性质和范围不同,当代公民不仅生活在民族国家内,还生活在公民社会和全球社会中,因此,当代公民应当是权利公民、国家公民、社会公民和世界公民四重身份的统一。公民教育应该在个人生活、国家生活、社会生活、国际生活中培养具有公民知识、能力、德行、能力的复合型公民。
[关键词] 公民身份; 复合型公民; 公民教育目标
[作者简介]冯建军(1969—),男,汉族,河南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哲学、道德教育研究。
公民既指向一种社会身份,又指向一种个体发展素质。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或法律身份,它由社会发展和国家政治制度所决定,但作为一种个体发展素质的要求,则是公民教育的结果。尽管对公民教育认识不同,但目标都是为了培养时代的理想公民,因此公民教育必须以理想公民的确立为前提。公民身份的确立和相应的素质要求,决定了什么是时代需要的公民教育。公民教育具有时代性,我们对公民教育的认识,需要首先从当代公民身份的认定开始。
公民身份及其素质要求不是固定的,而是历史生成的。它首先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其次是社会制度设计的结果。虽然古希腊时期,围绕着polis(城邦),出现了“公民”的观念,但严格地说来,“公民身份本质是一个现代的概念”[1],公民是现代社会人的形象,现代社会发展使公民的生活形态从共同生活到公共生活,也使他们的素质要求发生相应的变化。
马克思指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Individual),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越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由氏族间的冲突和整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 2]从最初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家庭,到后来扩大的氏族以及城邦,个人都不属于个人,而属于部落、氏族、城邦。中世纪又将个人异化为上帝,为上帝而生,也为上帝而死。从原始社会的自然依赖发展到古代阶级社会,皇权共同体取代了原始的自然共同体,自然的依赖关系又转变为人身依附关系。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个人只有臣民的身份,而没有公民的资格。臣民对统治者只有责任、顺从、服从,个人不属于自己,只属于他的“主子”。
所以,古代社会个人屈从于群体或统治者,是一个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臣民社会,臣民社会中人也是一种臣民的人格。公民不是臣民,要有一种独立人格。臣民没有独立的自我人格,失去了自由、权利和尊严,只有无条件的义务奉献。公民当以拥有平等的自由、权利和独立人格为前提。所以,马克思说,“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2]这个时候,才有公民产生的可能。
古希腊雅典的城邦生活,看起来是个例外。但准确地说,雅典城邦的公民是个特殊的身份,是根据腊自由人的男子才能获得公民资格,而妇女、小孩、奴隶和外来人则被排斥在公民行列之外。公民是一种贵族式或社会上层身份的标志,城邦生活只能说是那些特殊身份的公民的“公共生活”。对于雅典社会而言,公民之间的平等实质上只是“特定人群”的平等,对于公民和非公民而言,仍然存在着不平等和非公民对公民的依附和服从。所以,雅典的城邦生活,不是面向每一个人的公民生活,而是一种特定的阶层和群体的生活,不能成为现代公民社会的典范。从总体上看,公民与非公民之间没有脱离臣民社会的窠臼。
近代社会的公民,不是某一群体的特殊身份,而是面向社会的每一个人。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出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个人要走出古代社会依附性群体的束缚,具有自我的独立人格,并建立与他人的平等关系,维系平等的共同生活。这个意义上,正如特纳(Bryan S.Turner)所指出的:“公民资格实质上是现代政治的产物,即法国大革命与工业革命的社会政治结果……完整意义上的公民资格是封建与奴隶社会衰亡的后果,因此与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直接关联。”[3]
近代社会以工业化、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形成为标志,尤其是市场经济催生了人与人之间独立、平等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市场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只顾自己。把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利互惠、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情。”[4]市场经济对公民的社会的作用,一方面通过个人在交换中的自由、平等、所有权,催生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人格,使个人得以发现自我,并与作为自我的其他个人开展自由的交往;另一领域,同时,为了谋求私人生活的健全和不受侵害,又通过个人间平等交往建构起了共同生活的体系。但这种共同生活不是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私利、互利互惠而被迫共同生活,因此,人与人之间是以契约来规范共同生活的,这就形成了黑格尔所说的市民社会。“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达到目的的手段。”[5]
市场经济的出现,催生了近代自由主义的公民观。公民身份以个人自由、平等、权利为前提,作为一种法律身份,是依法自由行动且受到法律的保障的社会成员,社会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平等的自由和权利。所以,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认社会成员的公民身份及其平等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公民概念也逐步发生了变化,从共和主义公民观到自由主义公民观。最早产生的古希腊公民就是共和主义的公民观。共和主义的公民观以财产为基础,具有一定财产的人,才能自由、独立和平等,成为城邦的公民,因此,共和主义的公民观具有排他性。自由主义公民观是基于人人平等的理念,不论是否拥有财产,每个人都是合格的公民,所以,自由主义使公民从一种政治的特权和身份,变为一种法律的身份,法律保证人人平等。所谓的公民,就是拥有自由、平等权利的社会成员,这形成了权利公民的形象。英国学者T.H.马歇尔把公民身份分为三个部分或三个要素,即公民的要素(civil element)、政治要素(political element)和社会要素(social element)。“公民的要素”由个人自由所必需的权利组成,包括人身自由,言论、思想和信仰自由,拥有财产和订立有效契约的权利以及司法权利(right to justice);政治的要素,指公民作为政治权力实体的成员或这个实体的选举者,参与行使政治权力的权利;社会的要素,是指从某种程度的经济福利与安全到充分享有社会遗产并依据社会通行标准享受文明生活的权利等一系列权利。公民身份的三个权利维度是历史形成的,公民权利归于18世纪,政治权利归于19世纪,社会权利归于20世纪。[6]作为权利主体的公民,从18世纪的公民权利,到20世纪发展为三种权利并举,说明权利公民不只关注自我的权利,也关注共同生活的权利,反映了自由主义公民观向社群主义公民观的发展。
公民不是私民,必须以公共性为前提。但近代社会的共同生活,是基于个人主体的利益,公共性以契约和制度来维护。公民在共同生活中承担着消极、被动的角色,他们不是积极的公共利益、公共决策的参与者,不是基于共同善,而是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不得已共同接受一套社会规范,被动地共同生活。因此,近代社会的公民观是基于个人主义的,其核心是自我权力的平等。
当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人与人交往的扩大,共同利益的增加,使共同生活逐步转变为公共生活。共同生活是“形聚神散”,只是个人意志和欲望的集合体。但公共生活则不同,它是以公共利益、公共目标、公共善的存在为基点的。个体作为公共生活的成员,基于对公共生活目标的认同、公共价值的珍视以及公共生活的体验,个人融入到公共生活之中,这就形成了社群主义的公民观。社群主义在强调公民公共生活方面和共和主义一脉相承,但雅典的共和主义公民观具有排他性,而社群主义的公民观则是面向每一个社会成员。
自由主义立足于个人,认为个人先于群体,群体只是一种契约关系的临时存在。社群主义批判个人主义公民观只在乎个人的权利,而放弃了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忽视了公民的责任观念。社群主义认为,个体是社会的产物,社会决定着个人,因此,社会群体的利益先于个人。群体作为成员的共同生活载体,它不是众多个人利益的集合,而是群体的公共利益、公共善。所以,社群主义的出发点是社会,公民是社会的公民,他们具有对社会公共目标、公共善的认同。正因为社会的共同目标、公共利益、公共善,使他们成为一个整体,因此,社群主义的公民角色是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者。
社群主义认为,公民是社群的一个成员,他们之所以属于这个社群,不是出于对个人利益的保护,而是对该社群的认同。因此,公民之间需要的不是契约的约束,而是对社会的认同和德性。认同使公民具有了社群的归属感和忠诚,使社群成员之间具有直接的共享关系和共同的命运感,个人直接融入群体之中,群体的目标即为个人的目标,社会不是基于“众意”而是基于“公意”的公共生活。公共意愿的公共性来自于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公共利益,而不是参与者的数量。[7]
总之,公民身份的理论从古希腊的共和主义、近代的自由主义到当代的社群主义,并不表示后来的观念一定比前面正确。这些观念只是彼此修正、相互调整,社群主义承继了共和主义所强调的群体和公共善的理念,并且它们也是在自由主义体系内论述的。[8]所以,当出现社群主义时,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所强调的个人权利就失去了价值,恰恰相反,真正的社群是蕴含着个性和差异,以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为前提。如此,当代社会公民的身份虽然依然捍卫个人权利,成为权利意义上的个人公民,但人与人之间公共生活的增加,意味着公民之间不是一种单子式的“契约关系”,而是一种“共同体内的关系”。公民所在的共同体,从近到远、从小到大,有家庭、邻里社区、地区社会、民族国家和全球社会,人与人之间都是基于共同体内公共生活和公共善,成为不同社群的公民。
无论公民的公共性身份如何变化,但公民区别于臣民的独立、自由、平等人格的特征没有变。在这个意义上,公民不是臣民,首先表现为个人的权利主体。在公共生活方面,依据公民生活的范围,可以分为社会公民,即公民在社会中的身份要求;国家公民,即公民在国家中的身份要求;世界公民,即公民在全球社会中的身份要求。这就构成了当代公民的四重身份:个人公民(权利主体)、社会公民、国家公民和世界公民。
当然,公民身份的获得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法律和社会制度的保障性意义,要使这种保障性意义转化为一种实质性意义,必须将公民的身份还原为公民的素质,将社会制度的要求转化为教育的行动。正如帕特丽夏·怀特所说,“制度必须由具有健全精神的公民管理和使用。要适应民主制度下的生活,公民的确需要丰富的知识和技能,但是,他们也需要培养怎样民主地使用他们的知识和技能。他们需要民主的素质(Democratic dispositions)”[9]。
公民教育不等于公民道德(伦理)教育,公民教育的目标也不能只局限于道德教育。但公民又不能泛指一个完整的社会人,公民只是完整社会人的一种特定身份。所以,对公民素质的界定,既不能只狭隘地指向道德(伦理)素质,又不能泛化为人的一切素质。坎诺瓦(Pamela J.Conover)将公民素质定义为个人与政治社群之间的基本关系,而政治社群又是由成员与制度所共同组成的,因此,公民素质指的就是个别公民之间及其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他进而将公民素质分为法律的、心理的和行为的三个要素,法律的要素指向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心理的要素指向公民对社群的认同和公民意识,行为的要素指向公民在公共领域活动方面的实践,与公民德行有关。[10]28这一认识,较为恰当地界定了公民素质的范围,但公民的公共生活,除了政治社群,还有非政治的公民社会、全球社会。所以,公民素质指向处理公民之间、公民与社群之间关系的要求。这种要求不只是道德的要求,它全面地体现在知识、态度、价值、德行、能力和行为等方面,目的使公民获得对个人身份的认同,具有公共生活的知识、技能、德性和能力,积极参与公共生活。
公民所以成为公民,第一要件就在于他是人身与人格独立的权利主体。理解公民,首先要把握其权利本位内涵,它以公民的独立人格为前提,以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为核心要求。公民不是臣民,就在于公民是权利主体。自我权利的坚守,是公民资格的第一要素。即便是为了共同体的利益,也不应牺牲公民的正当权利。
权利主体的素质体现在:(1)知晓人权、自我的权利和义务,维护自我的权利和义务;(2)坚守“人是目的”的信念,捍卫人的自由、权利、尊严与独立人格;(3)具备独立思考的理性和明辨是非的道德判断力;(4)积极负责的人生观、价值观,自主自立、自律自省的能力;(5)自我的积极心理期待、理想、追求和自我实现;(6)独特个性、发散思维能力、批判力和创造力;(7)坚持社会正义和人类的真善美,具有正义感和道德勇气,见义勇为;(8)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履行公民的义务。
社会公民的生活范围是社会,社会是共同生活的人们通过各种关系组成的集合体,维持社会的纽带是社会关系。这里的社会,不单指当代西方所说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具有特定的内涵,它特指在政治领域和市场领域之外自愿结社、自由讨论公共问题和自主从事社会活动而自发结成的民间公共领域,包括个人私域、志愿者团体、非政府组织、非官方的公共领域、社会运动等。这里的社会不等于“公民社会”,但包括公民社会。社会不等于国家,国家是利益集团与政治的概念,社会是人与人之间广泛地普遍交往的产物,具有自愿性和平等性。维系社会的是共同的利益和公共生活。因此,社会公民就是为了社会公共生活的合作和共享而承担社会义务,为实现公正、平等的公共生活参与各种社会实践的人。公共生活是社会公民的前提要求,公共善和共同参与是社会公民的核心要求。
社会公民的素质体现在:(1)了解公民社会组织,掌握公共生活的知识和要求,尊重公共秩序;(2)尊重他人的权利与意见,平等待人,具有民主的意识;(3)相互关心,团结友爱,守望相助;(4)尊重差异,欣赏他人,宽容异己,包容多元;(5)认同社会公意,践行公共善,维护社会共同利益;(6)遵守社会善的要求,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正义感;(7)具有人道主义情怀,关心社会弱势群体,参与社会公益活动;(8)具有公共理性和有效的沟通表达能力、协调与解决冲突的能力;(9)热心社会活动,积极参与,乐意做义工和志愿者。
国家是一个政治概念。虽然它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不是永恒的,但现阶段却是一种主导的公民生活社群。每一个人都隶属特定的国家,形成其特定的国家公民身份。我们通常所说的公民,就是指国家的公民。国家公民根据该国宪法规定有权利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国家依宪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不受侵犯。国籍是国家公民的身份要求,认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维护国家的利益是对国家公民的根本要求。
国家公民的素质体现在:(1)掌握国家的政治、法律、经济、历史和文化方面的知识;(2)具有民族的自豪感、国家认同感和爱国主义情怀;(3)拥护国家的政权,维护国家的尊严,认同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4)坚持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同时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5)认同宪法,遵守国家法纪,具有护宪、守法的意识和法治精神;(6)具有民主意识、公共理性、正义精神;(7)关心国家大事,热心政治生活,具有民主参政的能力和对政府的批判监督能力;(8)参与政治生活,推进国家的政治民主和社会发展。
“世界公民”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它的谱系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也译为“全球主义”)。该学派认为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所以每个人也就是宇宙公民。对斯多葛学派世界主义的影响,美国学者卡特(April Carter)这样评价到:“斯多葛学派信奉人类的兄弟情谊、消除残忍和侵略、提倡宽容与慈善,为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典的世界主义思想的重新发现提供了基础。”它激励着后来的思想家对世界主义的信仰。[11]近代启蒙运动以来,一些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思想家,如康德提出了“世界公民”、黑格尔提出了“世界历史个人”,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敏锐地意识到“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趋势,也提出了“世界历史性的个人”。但公民身份的形成是需要外部社会条件的,在民族国家壁垒森严,国际交往贫乏的时代,世界公民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现代社会不同了。因为人类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世界已经变成了“地球村”,人类也面临着诸如全球生态危机、气候变暖、恐怖主义等共同问题,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世界各国必须协调统一起来,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因此,各国之间联系日益紧密,这也使得国家与国家之间从传统的竞争走向合作,人类利益的共同性日益增加,“全球公民社会”日渐形成。因此关于公民的认识,也必须超越传统的民族国家身份,树立一种全球视野、人类视野,关注全球事务并为此做出积极行动,这是世界公民对当代全球化的积极回应。根据英国非政府组织乐施会(Oxfam)的定义,世界公民就是将“世界视为一个全球社区并承认在这个社区内的公民所具有的权利与义务的人”。[12]
世界公民的素质体现在:(1)认识世界地理、历史、文化,了解全球化的发展,明白全球的相互依存关系;(2)树立全人类的整体意识,具备为地球上人们更好地生活负责的价值关怀;(3)尊重国际公约和规则,具有和平意识并致力于国际和平与发展;(4)尊重并欣赏他国的文化,具有多元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交流的能力;(5)认识全球化与本土的关系,具有本土文化的自觉意识和对异文化的开放意识;(6)关注落后国家和地区的贫穷与世界的不平等和不正义,并愿意承担责任,有效地参与,积极帮助弱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具有关心国际事务的热情有效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8)了解世界的生态危机,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具有保护地球家园的行动。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对公民身份与素质的认识,必须超越西方传统自由主义的“权利公民”形象,也必须超越西方当今“公民社会”的公民形象,还必须超越我国政治语境中的“政治公民”形象,要全面地考虑公民公共生活的空间,由近及远,由自己到他人、社会、国家、世界,确立个人公民(权利主体)、社会公民、国家公民和世界公民的复合形象,全方位考虑公民素质中的知识、态度、价值、德行、能力要求,培养具有时代气息、素质全面的当代复合型公民。
我国公民认识中的第一个误区是把公民当人民对待。“公民”是一个西方的概念,对我国来说,最熟悉的是“人民”,我们常常把公民的概念与人民混淆,以对人民的要求来对待公民。公民与人民不同,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一个群体性概念,是相对于“敌人”而言的。凡是人民,都属于一个政治团体,认同和拥护一个政治团体的利益。如当前一切赞成、拥护社会主义和拥护祖国统一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力量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人民强调其政治身份,保持与政治团体的高度一致性。因此,对人民的要求就是服从该政治团体的利益,必要时可以牺牲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人民是公民,但公民不一定都是人民,公民的范围要比人民大。公民和人民重要的不是范围大小问题,而是性质上的不同。公民是一个体的身份,是一个法律概念。按照我国宪法规定,凡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并依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享有一定的权利、承担一定义务的人,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公民是相对于非本国的外籍人士而言的。公民是国家的公民、国家的主人。公民作为主人委托政府管理国家,所以,政府的权力属于公民,政府应该为公民服务。国家和政府的利益应该是公民群体的利益,国家和政府不应该为了自我利益而牺牲公民的利益。公民的利益优先于国家利益,这就是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人民与政治团体的关系不同,政治团体的利益要优先于人民。所以,我们不能以对人民的要求来对待公民。
我国公民认识中的第二个误区是只把公民看做国家公民。我国对公民的一个最典型解释是:公民是指具有本国国籍,并依据宪法或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国家公民固然是公民的重要构成,但公民不只是国家公民,尤其是全球化时代,公民必须突破狭隘的国家公民,而确立世界公民的意识。传统的国家公民强调对国家的认同,强调国家利益至上,对国家利益的服从。这种认识不仅容易走向狭隘的国家主义,而且也容易忽视公民的个人权利。正是由于这一认识上的误区,我们才会把公民当做人民。
我国对公民认识的第三个误区是只强调公民的义务,而无视、回避公民的权利。权利与义务是紧密相连的,具有权利是尽义务的前提。如果公民缺少权利,就谈不上相应的义务。但我国对公民的要求,多强调的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爱国守法、敬业奉献,等等,这些固然属于公民的素质,但不能忽视要具备这些素质:要有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等。中国的封建传统道德维护的是一种严格的、以服从为特征的身份等级制度,其实质是:在赋予位尊者以绝对权利的同时,却对位卑者施以片面义务。在这种等级序列的人伦关系中,而只存在“特权”和“服从”,个人权利观念、权利义务平等观念自然无从谈起。[13]缺失公民主体和权利意识,所谓的公民只能是“子民”、“臣民”、“草民”、“顺民”、“暴民”、“人民”、“百姓”等,公民教育就成为了权利缺失的公民义务教育,这就成为了“臣民教育”、“顺民教育”、“草民教育”、“服从的教育”。公民不是臣民、顺民、草民、老百姓,就在于公民具有自我的权利,并且是公民义务的前提。
我们强调公民权利优先,但不是权利唯一,公民不能忽视公共性。公共性是公民的第二要件。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又暴露出公民认识的新问题: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的缺失。改革开放以来,强人政治结束,政治威权逐渐式微,社会日益向着自由、民主、多元与开放的方向发展,公民的权利意识、自由意识、民主意识逐渐增强,甚至有时达到了极致。个人意识的增强是必要的,但如果自由缺失了自律,民主缺失了法制,价值多元失去了价值底线、失去了社会认同,个人权利失去了公共生活,缺失了公共意识、公德心、责任感、公共精神,这样的公民必然是不健全的公民。公民首先是个体的公民,但不只是个体的公民,公民必须参与公共生活,维护公共利益,这是成为公民的第二个必要条件。当前我国的社会转型,唤醒了个人主体意识、权利意识,但公民的公共意识、参与意识和公共精神又出现了缺失。
根据时代的发展,我们强调当代公民必须具有四种身份,每个人不仅要成为个人公民,更应该成为国家公民(民族公民)、社会公民和世界公民。公民的角色由传统的国家政治成员(人民或国家政治公民的形象)发展为个人所属的群体成员的角色。个人所在的群体,围绕着自我,“由近到远”,层层扩大,由己到人、由他人到社会、国家,最后到世界、生态自然,公民的身份也由一元到多元,进而成为具有多种身份和素质要求的复合型公民。
公民的主体性与公共性是公民的基本要求。公民不是臣民,就在于公民首先是主体的权利公民,具有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捍卫并确保个人的权利是公民的第一条件,所以,公民必然具有个人性。但公民之所以是公民,不是私民,还在于公民具有公共生活,无论是自由主义消极的公共生活,还是共和主义积极的公共生活,公民一定在公共生活中,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服务于他人、社会、国家乃至世界。公共性是公民的第二特性。
复合型公民强调首先成为个人的公民,体现出公民的主体性。其次在社会公民、国家公民和世界公民中体现出公共性。公民的公共生活是为了维护个人的利益,因此其公共生活的范围由小到大,这意味着公民的多元身份中,个人公民先于社群公民,在三种社群公民身份中,国家公民先于社会公民,它们又先于世界公民,这是一个排列的词典式顺序。当各种公民的身份和利益发生冲突时,对前者的捍卫先于后者。公民首先是权利公民,然后是社群公民;先是国家公民、社会公民,然后才是世界公民。当它们和谐共存时,前者包容在后者之中。个人权利主体不是单子式的,而是社群中的主体间个人公民;国家公民不是狭隘的国家主义公民,而是具有世界意识的国家公民。当代公民的最终身份是世界公民,但世界公民不是全球一体化的世界公民,而是具有民族国家魂的世界公民。
复合型公民强调本土价值观与普适价值观兼并。关于公民,传统的认识局限于国家公民,强调公民的民族性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性。不同国家、意识形态不同,对公民的素质要求不同。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当代公民除了国民意义的公民身份之外,次国家意义上的社会公民和超国家意义上的世界公民身份意涵已经成为一种当代社会的现实。所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公民身份概念不仅具有历史特殊性和文化特殊性,同时也具有世界的普适性。[14]所以,复合型公民既要成为国家、民族的公民,强调民族和国家认同,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具有民族灵魂和国家意识,但同时,又必须超越狭隘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确立公民社会之公共生活意识、人类全球意识、地球共同体的生态意识,以及捍卫个人尊严的权利意识等;既要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强调的人类普适价值(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理性、权利等),又要反映儒家文化精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尤其是仁爱的伦理精神,把本土的儒家伦理价值观与普适价值观结合起来。复合型公民是超越国家政治公民的多元民主公民。复合型公民超越狭隘的国家公民,意味着对公民身份和素质的要求,就必须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观念。公民身份的多元,尤其是当代文化多元主义对差异性公民素质的强调,使当代公民必须确立多元民主的观念,强调具有“开阔的胸怀且具有包容多元(包括意见、文化、性别等差异)的平权思想与欣赏差异的能力,以及关怀弱势族群,重视人权与社会正义等”。[10]50
公民不因为具有一国国籍而自动成为公民,公民必须具备相应的素质,这就需要公民教育培养。公民教育不等于公民道德教育,也不等同于公民意识教育,更不等同于思想政治灌输,公民教育应该是一个整体的使“自然人”成为“公民”的教育。
复合型公民不仅强调身份是复合的,而且强调素质的复合,应该坚持公民素质的全面性。从形式上看,公民素质总体上包括认知、情意和行动,具体说来,包括公民知识、公民意识、公民德行与公民参与能力。所以,在形式上,公民教育内容应该涵盖公民知识教育、公民意识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和公民能力教育。
从内容上看,复合型公民素质涉及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民族)、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等多个方面,所以,公民教育的内容应该围绕着上述六大主题,从公民知识、公民意识、公民德行、公民参与能力四个层次,结合不同年龄阶段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特征,采用同一主题,螺旋上升的方式,设计公民教育内容。
正如一个人只能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在生活中学习生活一样,公民教育也必须通过公民的生活进行教育,在公民生活中学做公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中批评政治教育,“只谈论政治教育而没有进行政治中的教育”,“满足于反复灌输政治思想,而不去培养人们了解他们所处这个世界的结构,履行他们生活中的真正任务”。[15]这样的批评也同样适合于公民教育。公民教育必须走出公民意识的说教,而进入公民生活之中。根据复合型公民的四重身份,完整的公民生活包括公民个人生活、国家生活、社会生活和国际生活。我们必须根据每种公民生活的相应要求,引导学生过一种公民生活。在过公民生活的意义上,公民教育必须超越学校,更要超越课堂,走向真正的社会,因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践行真正的公民生活。
[1]布赖恩·特纳.公民身份与社会理论[M].郭忠华,蒋红军,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前言)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7.
[3] Bryan S.Turnerand Peter Hamilton. Citizenship critical concepts [A].General Commentary[C].London and New York: Rout ledge, 1998.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99.
[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97.
[6] T. H马歇尔, 安东尼·吉登斯, 等.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 [M].郭忠华, 刘训练, 编.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7-9.
[7]卢梭.社会契约论[M].庞姗姗,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39.
[8]林火旺.正义与公民[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163.
[9]帕特丽夏·怀特.公民品德与公共教育[M].朱红文,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2.
[10]张秀雄,李琪明.理想公民资质之探讨———台湾地区个案研究[M]//谢均才、刘国强.变革中的两岸德育与公民教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
[11]陈以藏.全球公民教育思潮的兴起与发展[J].外国教育研究,2010(3):66.
[12] What is Global Citizenship? [EB/OL]. http://www.oxfam.org.uk/education/gc/what_and_why/what
[13]王啸.公民教育:意义和取向[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0(1):20.
[14]檀传宝.论“公民”概念的特殊性与普适性[J].教育研究,2010(5):17-22.
[1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