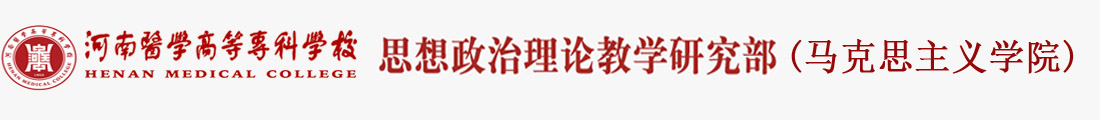人类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步入“和平发展”时代起,经历了两次较大的变局。第一次是90年代初,冷战结束,国际社会重组,形成以市场一体化为基础的全球新格局。今天,世界面临第二次变局。这次变局大致始于2008年西方反恐不力与金融危机,直至最近日本大地震与反恐局势演变,引发发达国家的总危机,并与新兴国家的崛起构成“此消彼长”的互动,从而构成国际社会战后罕见的变局。
总危机的直观性表象是发达国家生活质量的绝对下跌。10年前,这些国家基本都宣称进入了“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成长阶段。但近期的天灾人祸,包括可量化与不可量化的部分,正在使内部一直平稳、安逸的发达国家社会生活质量绝对下跌,这是几十年来没有过的。比如现在日本人在家需要两张图∶“地震预测分布图”与“核辐射超标图”,吃菜喝水都颇费思量。想出门到美欧躲躲,又需要一张“世界恐怖袭击警示图”。偌大的发达世界,竟容不下人们“衣食住行,平安保命”的最原始愿望。至于劳动安全、职业安全、生活稳定等就更难保障。这与一般周期性危机起伏造成的失业等明显不同。此次危机影响人多且不分族群。据学者统计,仅以核电站周边50公里为避难区,就将涉及1200万人,相当于日本人口1/10,这完全不同于一般偶发的局部灾害。正是这种战后从未有过的深度与广度,笔者认为应称之为“总危机”。
而总危机的参照性表象则是,发达国家综合国力的相对下滑,恰与中国等新兴国家的急剧崛起相反相成。这里不缺令人信服的经济数据,也有北京奥运、上海世博等直观场景,另外诸如率先走出危机阴影、举国抗灾体制等也令人印象深刻。这其中有偶然因素,也有10年来发达国家忙于“反恐”等形成的“此消彼长”效果,但最重要的是世界进入一体化格局后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律的全新作用。这次总危机的特征在于新兴经济体并非以“战争”、“重新瓜分”等方式挑战发达国家,而是在一体化的互惠合作共存中,通过静悄悄的和平竞赛形成亦友亦敌的博弈关系。各方实力消长的这种“非颠覆性”是对“和平发展”时代的细节诠释,而且呈现了某种“不可逆”的特征。
显然,此次发达国家的总危机并非一日之寒。据统计,至4月底日本已有66家企业受地震影响破产,总负债额超过人民币30亿元,这不能仅归咎于一次地震。日本著名历史学者川北稔震后撰文,以18世纪葡萄牙大地震比喻日本。美国人因击毙拉登而狂欢,但长达10年的“反恐包袱”依然压迫美国,即使奥巴马连任的“一家欢喜”,恐怕也难以消除200万失业者的“万家忧愁”。发达国家的复苏还有一段路要走,而且到走出阴影的那一天,也难保出现“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怕的就是一切已时过境迁。
面对这样的变局,发达国家普遍缺乏反省,依然以很大的惰性自行其是,这也是总危机的一个特征。日本地震后,政府及企业的对应迟缓备受指责。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在全球引发核危机,事发已两个多月,核危机已升至7级,但政府承诺设立的专门处理事故机构依然“千呼万唤不出来”。美国更是傲慢依然。奥巴马上台以来,人们没看到“巧实力”的多少内容,看到的却仍然是“以暴易暴”击毙拉登。这种强硬势必对国际局势产生影响。保守主义可能会再次上扬,反恐更加失去其正当性、合法性,美国与恐怖势力之间“扬汤止沸”的关系,让人们担心只会令总危机不断深化。
发达国家既不反省,又难忍危机煎熬,最有可能的做法是“内忧外移”,转嫁危机。5月9日从日本防卫省传出首次以“夺回钓鱼岛”为内容假想与中国发生海上冲突的作战方案,这个方案发生在日本震后,似乎不是一种偶然。美国去年以来在东亚为挽颓势,强硬介入中国周边一系列事态,就是先例。近日,许多人都在猜测美国击毙拉登后将重回10年前“遏制中国”的战略。其实这些年,发达国家始终没有放弃对付中国的“两把刀子”∶一是把经济低迷嫁祸于中国等新兴国家;二是以指责中国“人权”等弊端转移国内政治压力。特别是在中国等金砖“含金量”急速提高之际,奥巴马喊出了“美国不作老二”的口号。这种危机感必将加剧上述矛盾的烈度。
即便中国没有挑战美国的意图。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必须要有所准备。
首先是要有自信。时代变了,国际环境也变了,最重要的是中美关系也变了。10年来中美力量更均衡,中美关系更成熟,10年前那种保守主义泛滥的局面很难重演。今天的中国正值高成长周期之中,有信心也有能力应对变局。
其次是要冷静。要冷静把握这次危机不同以往的新特点,抓住全球一体化的本质与大局。因此,落井下石、以邻为壑显然不是好选项,现实的做法是积极捕捉我们与对方的共同点,争取共渡难关。例如,对方的生存危机与我们一直坚持的“生存权发展权”有共通之处;面对天灾人祸我们无疑具有极大的合作公约数;20国机制明显有利于缓解矛盾与危机,等等。对于转嫁危机,则应冷静区分哪些是合理的全球合作的要求,哪些是中国应有的改革与妥协,哪些是对方的无理挑衅与敌对行动。细心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妥善、有力、高效地对应。